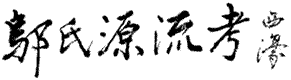|
梦想与超越 ——《奉化人》续篇
当我敲出“梦想与超越”这几个字时,我的眼前晃动着一批清末奉化人的身影。遥想当年,这批奉化人陆陆续续地从日渐凋敝的田野里起身,在令人断肠的血色黄昏里,肩背一袭褪了色的蓝布包袱(里边无疑有一把剪刀),手捏一柄旧油纸雨伞,告别妻儿老小、兄弟姐妹和乡邻们,从王溆浦、南渡、浦口王、江口、西坞、方桥、陡门桥、泰桥等或大或小的乡村或集镇码头,行色匆匆地登上人货混装的“夜航船”(或后来的“顺安”号“小火轮”);次日拂晓他们睡眼惺忪地从宁波外濠河码头上岸,甚至还来不及在码头边的小店里吃上一碗光面,又匆匆赶往江北岸码头,在那里裹进下饺子似的人流,钻进了令人头晕心昏的“上海轮船”统铺舱。然后,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落地生根,有一拨人在此歇一歇脚后,又北上海参崴,东涉日本,近赴港澳,远渡美加……就在这样的不经意奔波中,他们竟完成了一个奉化人实现梦想、超越自我的伟大壮举!
他们就是从奉化田野里起步的中国“红帮裁缝”先驱!
说他们从鄞奉平原寻常“夜航船”里开始的一次谋生旅程是一个壮举,我觉得理由是充分的。想当年还是清王朝的天下,漫长的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是农耕社会,万般以读书为高,以农为本。至今不用出奉化市区,就能发现一些铭刻着“耕读传家”的旧宅门第,岁月总要留下一些东西来印证自己的存在。耕可以获衣食,“学而优则仕”,所以被推崇。工匠历来被社会所鄙薄,能工巧匠至多只是些“雕虫小技”;商则更是被等而下之,行商必作奸犯科(所谓“奸商”)几乎就是那时的定论。但是当时到上海等地打拼的“红帮裁缝”先驱们所从事的则是前店后场的活计,也就是亦工亦商的角色,并且他们的技艺又不是师承本帮,而是师从外来的“红毛人”。参照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剧烈动荡和变革之中,国内革命或动乱的烽火不断,洋枪洋炮撞开国门,外来文化在“坚船利炮”之后又接踵而至,封建社会正在全面崩溃……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的这部分奉化先人决绝地与祖辈们一直辛勤耕耘的土地分手,走上了亦工亦商或介于工商之间的“红帮裁缝”之路,恰恰是踩准了当时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时代节奏!到今天来看,“红帮”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技艺、一种产业,而且发酵或积淀成了一种文化,成了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红帮”这种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求精求新,超越自我。求精是指他们继承弘扬了本帮裁缝精工细作的本色,求新是指他们敢于接受外来文化勇于创新,两者兼备才使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身份的历史性转换,完成了工商文化对几千年来农耕文化的历史性超越,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和重要的商帮!
“红帮”精神可以说是奉化精神之魂,是奉化数千年精神脉络延伸中一个承上启下的最重要的关节点。这一方面它不是无来由的奇峰突起,而是传承并集成了奉化历史上的各路精神脉络,另一方面它又对以后的奉化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走向产生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影响。这里暂不说无形的,就说具体有形的吧——奉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原始积累主要靠什么?靠的就是大大小小几百家服装厂的蜂拥而起,它不但有资本原始积累之功,更重要的还有效唤醒了千家万户的创业意识、市场意识。以精神脉络的层次而言,奉化改革开放的初航是百年前那“夜航船”的续航;奉化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初成果,是百年前“红帮”埋下的种子的萌芽。因此我坚持以为,“红帮裁缝”对奉化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只是我们对此还缺少应有的研究和认识。
“红帮裁缝”的发祥、发展,在历史长河里不是首次,而只是再一次证明:奉化人并非平庸之辈,他们是一群有梦的人,是一群有勇气和能力超越自我的人。
在追溯“红帮”精神的源头时,我们可以发现,在五六千年文明史的前半部分时间里,奉化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如早在五六千年之前,奉化的先民们创造了丰富璀璨的茗山后文化,奠定了奉化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地位。在距今4200年前后,当华夏大地大多数氏族还处在原始公社制的部落联盟时期,居住在浙东地区的古越氏族以奉化白杜为中心,又瓦解了原始公有制,率先建立起了奴隶社会的实体。这是目前可知的奉化最早实现的超越自我。
又如进入封建社会后,公元前222年秦设鄞郡,而郡治就在现在的白杜村一带。此后800余年间,古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是在别处,而是在今奉化的辖地内。正像我在《奉化人》里所说的那样:要论宁波的历史,必先论古鄞,而论古鄞历史,必溯源奉化。
但是,起点的辉煌,并不一定意味着以后行程会是永远的平坦。相反,历史已经证明,奉化人的超越之路是走得颇为坎坷的。
在白杜中心期后,奉化首先碰到了被边缘化。到了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鄞被并入句章县,所治已远离白杜,设到了小溪(即今鄞州区鄞江桥一带)……到公元738年(唐开元二十六年)时,明州已在三江口(今宁波市海曙区)设治了,奉化则已沦落到明州名下与贸阝、慈溪、翁山为伍的下属县之一了。今宁波辖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最初的白杜到鄞江,再到三江口,这条迁移轨迹,正好诠释了宁波区域文明逐步从逼仄的山区向开阔的江河海域伸展的过程,如果考虑到改革开放以后宁波又先后把甬江出海口的镇海、北仑改设为区,则这条轨迹就显得更为完美流畅。宁波的这条文明轨迹,与五千年来整个华夏文明的走向也是如此完美地相吻合……然而就在这个必然的文明演化过程中,相对于曾经有过的荣光,作为当年宁波文明发祥地的奉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就被边缘化了,这就像一个原来在舞台中央唱戏的角色被挤到舞台边缘跑起了龙套。
暂时的边缘化,对奉化人是一种失落,但他们所曾有过的不寻常的辉煌和荣光,在他们的脑际挥之不去,在他们的心头萦绕盘旋,他们的心里因此有了一个梦,一个曾经的贵族之梦!他们的胸间有一股子气,一股不服输的气!这就形成了奉化人最初不甘平庸的精神基因。这个基因就像一颗深埋的种子,一旦雨水适宜,它就会发芽、开花、结果……从百年前“红帮裁缝”的形成、崛起,我们可以穿越千年时空依稀看到那个梦的延续,感受到那一股子气的温度。
奉化的地理环境也为奉化人的超越之路设置了层层障碍。境内多山,为天台山脉与四明山脉的交接地带,其中四明山脉自嵊州由西向东延伸,主要形成与嵊州、余姚、鄞州界山,其中最高峰黄泥浆岗海拔976米,为境内最高峰,也是宁波市域内的最高峰之一;天台山脉自海拔945米的古镇亭山(现称第一尖)起向东北延伸,主要形成与宁海、新昌的界山。当你翻开任何一张奉化地势图,你都会发现奉化的南部、西部,西北大部都为高山峻岭所阻隔;而东部地区,在今同三高速公路以西的空间,十有八九的空间也为山地所覆盖;而那狭长的象山港,如今看来是一条黄金水道,但在那生产力低下的中世纪,除了能打点鱼,在对外沟通方面,它只能是一条令人望而却步的畏途;只有在中北部有一小块平原与鄞州相通——但同时老天爷又没忘记设置了对当时来说显得过于宽阔的剡江、东江水面与之相隔。可谓不是山挡就是水隔。总之,放在中世纪的背景里,奉化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封闭性极强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多多少少会给生于斯长于斯的奉化人染上点闭塞、保守的痼疾。天长日久,有不少的奉化人因此而染上了“埠头黄鳝”和“打煞老鼠不离窠”的心态——这也就是我说的奉化的地理环境也为奉化人的超越之路设置了层层障碍的意思。
但是,祖先有过的荣光使后来人的心里早就埋下了不甘平庸的精神基因。地理环境的呈包围状态,同时也促成许多奉化人萌发了强烈的突围欲望。
从哪里突围?奉化人看准了中北部一隅的平原,更准确地说是看准了那里曾是阻隔的水路。剡江、县江和东江三大水系,囊括约占奉化总面积四分之三的流域面积,三江自南部、西部、西北山区向东、向北奔腾而下,在奉化北部三江平原北端的方桥三江口相聚,汇合成奉化江,再在宁波三江口与余姚江相会,汇合成甬江,流入东海,融入茫茫太平洋。看中这样一条水道,是奉化人的慧眼所在。所以,自唐宋以降,奉化的内河水运一直比较发达。
唐代境内就有驿道相通,而进入奉化境内的驿路首站就是北渡;自此之后,它一直是鄞奉共管的著名渡口,也是奉化最重要的渡口之一——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单位的一个同事每到周末总是乘汽车到鄞县横涨,再在那里经横涨渡摆渡到老家胡家村,那时奉化全境还有11个渡口,北渡、横涨渡就首列一二(不知如今此渡是否还在)。在当时的三江中下游的溪流河网里,竹筏、乌山船、百官船、夜航船……可谓是百舸争流。奉化西部山区的山货,甚至周边新昌、嵊州、宁海以及其它西南诸地的山货、缸甏之类,经溪口、泉口(萧王庙)、江口、大埠、大桥、西坞这些集散地下船,流向宁波及更远的地方,而返程的时候它们又满载着食盐、棉布、医药等山民生活必需品逆流而上,因而造就了当时上述之地的繁华和相对繁华。这些至今大部沿存的地名,特别是大埠、西坞这样的地名,本身就说明了当时这些地方水运发达之程度。
这种发达在清末民初被发挥到了顶点,当时西坞乡绅邬谟贤等人合伙购置了小汽轮,开起了轮船公司,随后又有三艘每艘定员200多人的轮船投入西坞至宁波的航运,西坞一时繁华而被人称之“小宁波”……后来,因为垦山加剧导致生态受损,江道沙石沉积,再加上鄞奉公路的开通,奉化水运才走向彻底的衰落(一度热闹的萧王庙、西坞也随之堙没无闻)。
从奉化水运的曾经繁荣,我们看到了奉化人怎么样把自然环境的天然阻隔转化为沟通的便利的努力及其成功,从把一线水路经营得有声有色这一突围实践里,我们依旧看到了奉化人那种不甘囿于一地、勇于超越自我的那份精神基因。至今我仍会遐想: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道水路,“红帮裁缝”的发祥地也许就不会在奉化……
历史的长河有波浪滔滔的时候,也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在唐建县以来的1268年的历史里,奉化在多数的日子里是默默无闻的县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没有多少可供它上演的戏。但是至少有两个时期奉化是出类拔萃或令人瞩目的。对这两个时期作一简单的回顾,我想是会得到有益启示的。
一个是在南宋至元,像舒璘这样的一代理学名家和像戴表元这样的“东南文章大家”就出在那时,戴与当时的文豪黄 氵晋 、大书法家赵孟兆页 三人聚讲于县西法华寺朝晖轩,黄、戴作诗文,赵书之,时人称之为“三绝”的佳话也发生在那时。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在惟以读书致仕为高的封建大一统背景下,舒璘一家三代竟有六人考中进士,并在朝中做官,时人有“舒半朝”之称。当时的奉化可谓是人文荟萃,而且经济发达,以至于到元元贞元年(1295年),奉化被提升为州,直到六十多年后的明洪武二年才复降为县。这一时期无疑是奉化中兴的黄金时代。
另一是在清末民初,经过明清几百年的寂寞,奉化忽然又涌现出一大批在周边地区以至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的著名人物,这在宁波府各辖县中是独领风骚的。如在教育界,有力倡新学的光绪进士、民初浙江省教育会长萧王庙人孙锵,曾任龙津学堂舍监、激励学生反清爱国、出洋深造的裘村人庄崧甫(同时他还是农学专家和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宁波最高学府宁波中学堂监督的“奉化三江”之一的江口人江北溟清末就在奉化龙津学堂聘日籍教师讲授数理化和日语、英语,等等。在科技医学界,马头的陈滋在清末就赴日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开设眼科医院,是国人创办西医眼科医院之始,也是国内学界公认的以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的先驱——十多年前我在上海陈老先生后人(交通大学教授)的家里还曾看到了他留下的许多著述的目录;如萧王庙的孙海环,在国外攻读采矿冶金专业,民初回国后,效力国家实业,并独树一帜发明了有“孙炉”之称的炼铜炉;又如桐照的林平一,20年代就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受到重用的水利专家,等等。
当时的奉化人文荟萃,最为直接的体现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工商实业界,如有创办民丰、华丰、云丰造纸厂等实业的著名爱国资本家萧王庙人竺梅先,其中他和夫人徐锦华女士在抗战时期在奉殚精竭虑,自费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供养、教育600余战时孤儿的事迹,尤为感人——笔者清楚记得十多年前台湾作家彭竹予(当年教养院学生,其笔名寓意就是我姓彭的生命是竺梅先给予的)对我说起竺梅先事迹时不禁老泪纵横的感人情景;如开国人办冰冻业之先声,在欧美诸国设分公司、分理处,任中国冰蛋业公会会长、世界蛋业公会理事长的“蛋大王”萧王庙人郑源兴;如创办华孚金笔厂,使华孚金笔跃居上海四大名笔(金星、华孚、博士、关勒铭)之一、1950年又捐巨款抗美援朝的北门村人周荆庭;如曾任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市花树同业公会首届主席的园艺专家和实业家萧王庙人黄岳渊;而以江口人王才运为领军人物的“红帮裁缝”的崛起,更是奉化人对近代中国工商界所作出的最巨大的贡献。
二是在政界,有早期同盟会元老东门村人周淡游、白杜税务场村人王正廷,其中王曾是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在和约上拒不签字的“不签字代表”,曾兼代国务总理,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终身委员等多职,而蒋介石及其俞飞鹏、朱守梅、俞济时、俞济民,毛邦初等一大批奉化籍民国军政要人,则是他们的后来之辈了;而有意思的是,在共产党一方,也出了不少著名人士,如大革命时期浙东工人领袖、烈士王鲲,同时期的团中央委员、团湖北省委书记、烈士卓恺泽,早期浙江省委书记、烈士卓兰芳,中共七大代表、马列主义哲学家、翻译家吴亮平,中共党史专家胡华,著名文学家巴人……
宋元和清末民初,是奉化历史上应该大书物书的时期。为什么奉化的历史长河流经这两个时期,会溅起这么大的浪花?我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但以我的粗见,发现这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剧烈激荡。
先说宋元,特别是由于北方金兵入侵,在北宋末年,北方士民开始避乱南迁;及至南宋时期,随着宋朝首都迁至临安(今杭州市),大批北方士大夫以及其它各式人等的南迁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东南之地一时喧哗、繁华。也有大量的北人涌入了奉化。据记载,宋天禧年间奉化始记载户口时,奉化全部人口也就8161户,16616口;到北宋政和年间,不到一百年的功夫,就激增至28033户,61270口;而到元至元(1264-1294)年间又激增至48352户,262820口——这个数字在以后的600余年间一直未被突破过,并相当于1901年时的奉化全县人口。大量北人迁入奉化,挟带来大量的北方文化元素,它们与南方固有的文化元素、奉化的地方文化元素相互激荡相互交融,产生了新的活力。所以,当时奉化人表现出来的巨大包容性(接纳了这么多北人)、主动接受北方文化的精华,才是宋元时期奉化经济、社会、文化出现景气的根本动因。
再说清末民初,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宁波的近邻,且又是甬方言区的重要组成区域(余慈地区则更多地属于越语区),加上当时以西坞、大埠、大桥为代表的奉化与宁波间水上航运(当时宁波各县均无公路)的通畅便捷,自然使奉化得了开放风气之先,新思潮、新文化传入奉化相对较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县内的最高学府龙津学堂,在清末就已聘请了两名日籍教师进行新式教育(事隔近百年后市内的东方外国语学校才聘了一名外籍教师,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奉化人的开放),当时的学堂主管又都非常睿智开明,他们对清政府强烈不满,大力鼓励年轻学子出洋留学,寻求新知识,寻求救国之道,以至当时有一大批龙津学子先后赴洋深造(包括蒋志清——即蒋介石)……在那激烈动荡、变革的时代,在奉化优秀人士主持下的龙津学堂在开启民智、孕育优秀志士人才、接受新文化新思潮等方面为奉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由此也可见真正的教育对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之巨大!
综上所述,只有以前瞻的目光和宽阔视野面对世界变化大局,以兼收并蓄的气度顺应时代潮流,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地方的繁荣和发展。应该说,那时的奉化人做到了。
当代奉化人必须牢记这个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说到当代,我以为,当年许多制约奉化发展的因素已不复存在,奉化的发展在当前已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关口。
首先来看一下上文提到的历史上一度被“边缘化”的问题,对如今的奉化是否还存在?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奉化大地:在中北部平原,宁波几大工业园区之一的明州工业园区和鄞奉产业集聚区已涵盖到奉,奉化高新技术园区已见一定规模;在东部港湾区,松岙临港工业带建设已经实质性启动,莼湖一带已被初定为宁波市象山港休闲度假区的首先启动板块;在西部,溪口雪窦山景区已成为国内旅游热地。年前召开的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又提出了把奉化建设成为宁波南郊现代化生态城市的目标,“融入宁波,接轨宁波”战略已不断深入人心……奉化在宁波都市圈建设的舞台上已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边缘化”现象已荡然无存。
回过头来看,历史上自然环境对奉化超越之路的障碍也已不复存在。除了分别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和六十年代末开通的鄞奉公路(现甬临线一部分)、奉新公路(现江拔线)和浒溪线这三条省道公路外,近年交通建设出现突飞猛进之势,新开通的同三高速、甬金高速大气磅礴地穿境而过,甬台温铁路建设也已正式启动,并将在境内设站,第二条铁路甬金铁路也已在蓝图设计之中,国际机场、海运港口又在咫尺之间……天堑变通途,当年的险阻早已成昨日黄花,当年封闭性的环境如今已成四通八达的宁波近郊。
无庸讳言,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在有形无形和有意无意地影响、制约着奉化的发展之路、超越之路,那就是存在于我们头脑里的某一部分东西。
纵观奉化历史,我们有起步阶段茗山后文化的璀璨,白杜中心时代的荣光,宋元时期中兴的繁华,清末民初时的兴盛。但令人扼腕的是,曾几何时,由于此地曾是“蒋介石的老窝”(当时语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奉化受到了比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更大的政治压力,精神上也受到更大的挫伤。就像民国时期奉化人出外操一口奉化话就能得到礼遇一样,而此时的奉化人则是要遮头掩面了。奉化人的精神从高山之巅一下子跌落到谷底,失衡中产生扭曲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奉化人的精神脉络到此突然产生错位、撕裂。这是一种内伤,没有一定的时间代价,是不易发觉它的痛处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奉化人还一时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这是奉化人心里深深的痛!
这种精神脉络上的错位、扭曲,影响是深远的。直至到改革开放,人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许多奉化人却还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还在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生怕惹事,生怕犯错,甚至自寻烦恼,自设障碍。我在《奉化人》中曾写到:“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曾几何时,我们不知怎的竟比别人慢了一步或半拍:当激烈的竞争悄悄找上门来时,我们还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对悄然来临的挑战和潜伏的危机缺乏应有的敏感;当别人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时候,我们还在以国营集体企业占大头为荣;当别人在搞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时候,我们还在向濒临困境的国集企业输血……”其实我在那里所说的还只是近距离的表层原因,深层的原因是奉化人历来就具有的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被那个特殊的时代扭曲了,隔断了,以至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时,许多人的意识还可怜巴巴地留在那个噩梦里不能自拔。
譬如:我们曾有的大气不见了。遥想20年前华谊大厦矗立,南山路拓宽之时,许多“革命”同志就指责“有必要大厦造得这样高、马路造得像机场跑道吗”?以至在一段时间里,奉化的路越造越小。记得在拓现奉化剧院西侧一段路面(锦屏北路末端)时,也许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驾摩托的一个机关通讯员向领导反映这路规划得太小,领导竟感到十分惊奇:“农民上城卖谷,有两部手拉车可交会,这还不够宽啊?”奉化城建的“胎里病”在那时已落下了。
譬如,我们曾有的宽容的胸襟变小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在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本地一旦有什么新举措出来,有的人只要一看不合自己心意,不合自己的“标准”,马上就八分邮票(时价)一枚告你一状,给你一个举报,弄得干事的人心灰意懒。甚至当年奉化第一高楼华谊大厦落成时有关部门放了点焰火庆贺(当时大厦是国有体制),也有人以“铺张浪费”之名告到宁波、杭州……
譬如,我们曾有的开放气度丢失了。记得在大约才10年前,一批金华布料商慕奉化是服装名城,于是进驻当时的奉化服装城做起了生意。他们的生意倒是红红火火,但一些奉化人的眼也随之红了,于是寻衅滋事、拳打脚踢,把金华布料商扫地出门才罢休,此事经各路媒体报道,一时沸沸扬扬。
譬如,我们曾有的拚搏创业氛围淡化了。一些人宁可在本地终日游手好闲、瞎混混,也害怕到处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有钱存银行或购房产以获取利息、租金的人,远远比投资实业的人多。历史上封闭性极强的地理空间造成的“埠头黄鳝”和“打煞老鼠不离窠”的劣根性被放大了。
譬如,我们曾有的吃苦耐劳的美德被消解了。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下岗、无业而处在相对贫困之中,另一方面是有许多就业岗位而不肯低就。市区的三轮车“踏哥”已换了一茬又一茬,先是市区里的换给市郊的,后来是换给边远农村的,现在几乎是外省人的一统天下。这一来,有时坐三轮车乘客还不得不给“踏哥”当向导,成为奉城一奇。
譬如,我们曾有的不甘平庸的气质萎缩了。至今仍有一些男子汉为“灶间厨下 做做饭”,“小店铺里坐坐搓搓小麻将”而心安理得,而他们的妻子或女儿却在服装厂日夜班轮番劳作。
……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前期还存在着以上这样那样的“譬如”,主要还是客观历史因素在起主导作用,那么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有这样的“譬如”存在,那就需自己深刻反省的了。好在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奉化人的精神风貌很多方面已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或正在得到改观。奉化人被扭曲的精神像一种有记忆力的金属材料,正在逐渐复位。我们也可以俯拾几个“譬如”:
譬如,引进波导的成功,预示了我们曾有的大气又开始回到我们的身边。
譬如,创造条件启动并成功实施县江改造工程,显示我们的手笔正越来越大,早已与当年非议南山路的小家子气挥手作别。
譬如,滕头村几年上一个台阶,面貌不断换新,十多年前跻身“全球500佳”,去年成为首批全国文明村,诠注了奉化人有不断进取的能耐。
譬如,全国创新的“力邦村”模式诞生在奉化,说明我们的创新精神和在宋元时期就有的巨大包容性和人文关怀正在很快恢复。
譬如,奉化的特色农产品的品牌越来越响,盘子越做越大,收入也随之增多,这是我们曾有的求精做精禀赋的体现。
譬如,近几年奉化在全国百强县中的位次不断提前,证明了不断超越自我的“红帮”精神已在我们眼前闪烁。
……
奉化是一个有魂有魄的地方,这个魂魄就是它数千年来的精神脉络,就是它不断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这条心路历程是坎坷的,但走向是清晰的;这条脉络虽然出现过扭曲和断层,但断裂只是暂时的,延续是永远的。
在我心中,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广袤的奉化大地和它的历史纵深处。这个悠悠的梦,也是全体奉化人的梦。这个梦里回荡着一个声音:
奉化,魂兮归来!
|